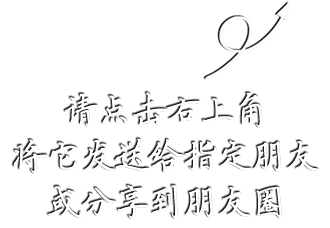长情如文火 遂昌行游记(序)
序
是哪处曾相见,相看俨然

袅晴丝吹来闲庭院,摇漾春如线。
第一次到遂昌,正是这样的暮春时节。熟路的朋友领着我们往汤显祖纪念馆去,在县城北街旁窄窄的小巷里穿行,拐几个弯,右手边有一扇敞开的黑漆院门。
迈过低低的门槛,第一眼打量这个院落时,却想起《牡丹亭》里的一折,女书生杜丽娘于花园之中凭几而眠,莺啭梦回,初初与柳梦梅相会,二人心下皆惊:
“是哪处曾相见,相看俨然?”

纪念馆的建筑是明清时期的老宅,外头围墙上留着花窗,砌了人物与故事塑像。那就是汤显祖笔下的“临川四梦”,分别是《牡丹亭》《紫钗记》《邯郸记》《南柯记》,也称“玉茗堂四梦”,因四个故事中皆有梦境而得名。
老宅白墙黛瓦,院落小小,草木茵茵,过了庭院往前就是堂屋,有一幅汤显祖画像居于其中。这幅画像是现今唯一存世的汤显祖画像,来自俞平伯先生的收藏,俞先生从小听昆曲长大,建国后,《牡丹亭》亦是在他的主持和倡议下,以全剧的形式再现舞台。
旁边的展厅则是陈列室,介绍汤显祖生平和在遂昌的政绩,以及他的艺术创作和后人的评论研究。小小的展厅里,整齐陈列着文人墨迹、旧时书简、舞台照片,过往的岁月隔着几十、几百年的物是人非,在这里重聚,还原出汤显祖的一生。
我最喜欢的,是那几本《牡丹亭》工尺谱,泛了黄,有虫噬过的小洞,边缘仿佛被灼烧过一般微微卷起,那上面是娟秀的小楷:但是相思莫相负,牡丹亭上三生路。

相思莫相负。
四百多年前,汤显祖在遂昌做了五年县令,说起来,时间并不长,而遂昌人对他的思念和纪念,却一直绵延至今。
汤显祖是明代江西临川人。他出身书香门第,早有才名,不仅于古文诗词颇精,而且能通天文地理、医药卜筮诸书。34岁那年,他中了进士,在南京先后任太常寺博士、詹事府主簿和礼部祠祭司主事。明万历十九年(1591年),他目睹当时官僚腐败,愤而上《论辅臣科臣疏》,触怒了皇帝,被贬为徐闻典史,后调任遂昌县知县,自此,一任五年。
遂昌居于浙南群山之中,土风淳美,却赋寡民稀,学舍、仓庾、城垣俱废。汤显祖到任之后,建射堂,修书院,下乡劝农,闲时则与人切磋文字。如此几年,桑麻牛畜都兴旺起来。
然而出来为官,便难免政敌,万历二十六年(1598),听说朝廷将派税使来遂昌扰民,他不堪忍受,便向吏部递了辞呈,也不等批准,就拂袖而去,回到家乡。

自别后,倏忽四百余年,遂昌人对这位仁政爱民的县令的纪念,未有过一时停息,除了纪念馆,还修建有遗爱祠与遗爱亭。
也正是汤显祖,把昆曲带到了遂昌,民间演唱昆曲一时风靡。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,它仅局限于小部分人。如今,在每年春天举办的“汤显祖文化节”上,昆曲又成为重头戏。在刚刚结束的这一届上,最大亮点便是万人齐唱《牡丹亭》。除此之外,还举办了“班春劝农”典礼、昆曲大奖赛、汤显祖文化艺术展等活动,重现400年前汤显祖在遂昌执政时期“政通人和”的和谐场景。
还有不得不提的,是这些年来让许多年轻人认识昆曲、沉醉昆曲的青春版《牡丹亭》。它由两岸三地艺术家携手打造,由著名作家白先勇主持制作。馆长谢文君回忆说,当年她在北京与白先勇第一次见面时,他第一句话便问她:“你喜欢昆曲吗?”后来,白先勇亲自来到遂昌,来到汤显祖纪念馆。先生是一个对昆曲痴迷的人,在他看来,到纪念馆来就是一种朝圣,他认为汤显祖是昆曲的祖师爷,来到这里,就仿佛穿越了时空,和400年前的汤显祖对话。
和白先勇先生一样,每年专程来到这里的,还有内地和香港、台湾的专家学者,全国各地的昆曲团团员,大学里研究戏曲的学生,他们纷纷来此缅怀纪念汤显祖。更让他们惊叹的,是纪念馆二楼的一万多册珍贵藏书,每每勾留,不忍释卷。

馆长谢文君从1994年就在纪念馆工作,从做讲解员开始。对当年做着舞蹈梦的她来说,这里的日子太安静,太寂寞了。二十年间,她在这里做的最多的事,就是看书,看书,再看书,让心安静下来,然后,再也离不开。
谢文君说,这里的宁静安详的氛围还得益于这座建筑。古建筑是要养的,每一个细节都是如此。比如打扫卫生时,不能用水洗,只能擦出来,她们就用布一点点擦干净。还有一次布置民俗展,是根据明代摆设做出来的,既不能违背建筑本身的格局,陈列物又要搁进去,为此,她没少跟布展的师傅争执,像铁钉子,就是一根都不能钉的。如此,在每个角落都最大限度地保护建筑本体,然后,每年去添一些与汤显祖文化有关的东西进去,就够了。
比如侧面那一小间琴房,还原的是明代人下棋、弹琴、喝茶的生活场景。背景中一枝梅花,明眼人看到,便会想到柳梦梅;还有后院的小花园,回廊的那一头,有座小戏台,挂着出将入相的门帘,上面的匾额写着四个字:姹紫嫣红。
闭上眼睛,仿佛就听见《牡丹亭》咿咿呀呀唱起来了。